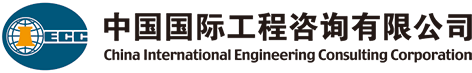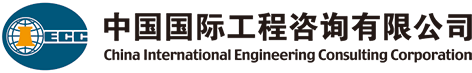我国能够兼顾短期和长期,将市场的短期理性与规划的长期理性有机结合。规划体制使得中国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谋划长远,布局未来。“家有千件事,先从紧处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业待兴,经过“一五”到“五五”5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制定“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同样是“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在规划未来五年发展的同时,瞄准2035年远景目标,前瞻性部署一批战略性产业、基础性工程。
我国能够兼顾微观和宏观,将市场微观理性和规划宏观理性有机结合。市场机制能够运用分散信息,通过分散决策来实现微观理性,而规划机制能够运用整体信息,通过整体筹划来实现宏观理性。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但需要企业自身竞争力,而且需要通过规划引导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光伏发电、无人机、5G、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后来居上,除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企业家创新精神,鼓励不同路线、不同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国家规划对于产业政策的系统设计,对于基础设施的前瞻布局,以及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的长远谋划。
我国不但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微观均衡,而且能够通过规划体制引导宏观均衡。我国运用规划调控来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拉动经济增长,避免了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比如,“十三五”以来,我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提升了有效供给,扩大了有效需求,推动实现总量均衡。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矛盾进一步凸显,“十四五”规划针对这一突出矛盾,鲜明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等大范围空间布局,也并不是市场机制能够自发达到均衡的,需要五年规划的有效引导。比如,我国营运里程接近5万公里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输电通道总里程突破5万公里的特高压电网,正是通过五年规划前瞻布局、科学规划、有序实施的结果。
四、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五年规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有利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五年规划系统设计公共政策,集成任务举措,对接项目布局,对于一揽子政策进行通盘部署,避免了政策碎片化和相互冲突。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五年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级、省级、市县级规划共同组成的三级四类的国家规划体系。加强五年规划战略导向功能,能够引导各级各类规划各司其职、贯通衔接。高效能宏观经济治理需要财政、货币、产业、土地等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相互配合,加强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优化规划与宏观调控联动,能够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放大叠加效应,避免不同宏观政策之间的“合成谬误”。
加强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能够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稳定性。我国形成了“长规划、短安排”机制,引导资源跨周期配置,加强逆周期调节,能够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稳定社会预期,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五年规划的政策和项目储备,能够为宏观调控提供“弹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例如,针对2024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面临的较大下行压力,党中央果断决策,及时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抑制了外部冲击,实现了5%的增长,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有机衔接,相当部分措施已经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只不过是借机加快推进节奏。过去10年,全球经济增长非常不稳定,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稳健的大国之一。
按照五年规划绘就的蓝图推动发展实践,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能够做到一届政府接着一届政府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五年规划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一个中长期锚点,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有机衔接,宏观调控能够做到长短结合。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换一届政府就“翻一回烧饼”,不是接着干而是对着干,宏观政策左右摇摆,缺乏基本政策延续性。
总之,五年规划是中国之治的重要体现和突出优势,将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已经创造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发展规划,有力推动了国家发展,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我国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构建更好的经济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